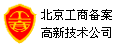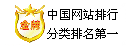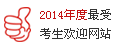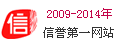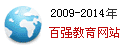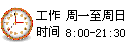刘 那时你还没有开始拍片子吧?
冯 没有,只是跟他做些翻译
工作。比如我们去拍一个专门研究哈萨克民族
文化的老头,采访完那老头,野中也想采访一下老头的夫人,这在成片里顶多只用几分钟。但野中跟那老婆的采访,整整录制了6个小时。因为那老婆特别孤独,早年那老先生在监狱里待了好多年,出来之后已经八十多岁了,就想赶紧干自己的事,根本没有时间理老婆,他们俩一天也说不了几句话。我们在那几天,老太太特别紧张,而且跟我们有距离。采访老婆那天,野中就一个原则——让她彻底痛快地说。结果老婆可找到一个倾诉对象了,跟我们说了很久很久。我就发现,老婆倾诉完之后,你看她的眉眼都变化了。野中不是那种“掠夺性”的采访,问完
问题就完事了,而是用这种方式来对待他的采访对象,这让我觉得这个人太值得尊敬了。
刘 关于这一点,我也很有感慨。我们所看见到那种掠夺性的采访、功利性的采访、做秀式的采访、扭曲式的采访,太多了。这倒不是说,我们不看
节目样态,不看具体情况,一味都采用这种长时间的采访就叫“不掠夺”,不是的。从野中章弘的做法中,我们看到了他对被采访者的态度以及用心程度。
冯 是的。后来回日本之后,野中希望我也能拍片。正巧,我日本的房东,他特别喜欢摄影,在他的引导下我开始拿起摄影机拍东西。以前,走在马路上,过来什么样的人你不会感兴趣的,等拿起摄影机以后,你突然觉得,也许这个人会有故事,你会有所发现,就突然觉得世界变得丰富多彩起来。
刘 这样来看,1993年真的成了你生命里的一个转折点了。这样,你就“改行”了,不当你的经济学学者了?
冯 那一段时间我都处在一种特别震撼的情绪里。原来还有这样一个充满了魔力的神奇世界!在这样的纪录片里,我找到了一种更符合自己内心需要的生存方式。我开始在日本给朝日电视台的“自由层”拍一些片子。我觉得:人呐,只要有点儿价值,哪儿舒服就往哪儿走。在三峡,拍那个老奶奶、拍张秉爱,我觉得都是因为她们需要我,我就觉得挺舒服的。不像我在学校里,非要写一篇好的论文给老师,老师才会表扬我,不用那样的。
 1124768988(合作加盟)
1124768988(合作加盟)  353157718(技术支持) Email:1124768988@qq.com
353157718(技术支持) Email:1124768988@qq.com